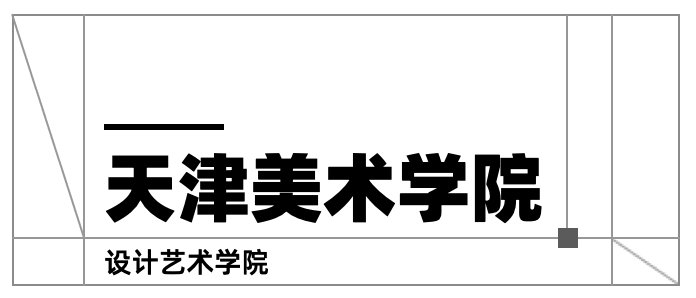
我是1973年进入天津美院学习的,属于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留校工作。那时,老师和同学就像朋友一样,关系特别融洽。我们没上过大学,也没见过大学教授,所以见到天美的老师,由衷地敬佩和敬重他们,教学、谈心、下乡生活,这些活动让人很享受。孙其峰和溥佐两位老师教授国画课,经常画一大摞手稿给我们看。除了听课,我们还天天临摹,经常画到半夜。霍春阳老师,染织专业的苏宝礼、陈重武老师带着我们一起下乡写生,同吃同住,师生感情很浓厚。
我正式学习纤维艺术是出国以后,在国内其前身是染织专业。天美的染织专业最初以服饰图案和室内装饰小壁挂等平面设计为中心。20世纪70年代,我去上海进修花布图案设计,回来后将上海的设计风格带到系里,提倡与工厂相结合,后来,我们的设计图纸参加选花会并多次被选中。七八十年代,老师经常带学生去云南、贵州学习蜡染和扎染技艺,回来后在染织教研室做扎染和蜡染工作,学生设计从纸面走向实物,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天津电视台还为我拍摄了相关工艺制作的讲座视频。此后,我的染织作品变得更加丰富,增加了丝网印,但我还没接触过立体的纤维艺术。后来,我开始学习日语,先是自学,后来系里支持我去天津外国语学院学习,之后就准备考试出国留学。
我刚到日本时,对老师的艺术作品看不懂,他就说现在看不懂就别看他的作品了。作为一名在中国深耕染织专业十几年的大学教师,到了日本却被老师这么奚落,我心里感到特别难过,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转念一想,如果努力学习不可能不懂。从那以后,我开始尽可能多地参观各种展览,还积极地参与展览的筹备工作,从搬运物品到布置场地再到开幕式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兴趣,也开始想去研究,但我最初的作品跟绘画和图案联系得很紧密,不能一下子进入新的状态。于是,我开始用织的手法去做,体会与图纸和画面不同的感觉,像蜡染和扎染是在平面上,而现在是用织的手法在布上创作图案,这是提前设计好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也一点点地深入其中。
1992年,浙江举办了一个丝绸研讨会。我陪导师一起参加完研讨会后,利用空闲时间去参观了周边地区,包括弹棉花的地方等。我们还去了黄道婆的家乡,观看纺线等民间工艺。从那以后,我对纺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与我的专业联系紧密,对我的作品会更有意义。回到日本后,我开始学习纺线,从用纺线锤开始,将棉花放在手中转动纺锤,让线变细并缠在纺锤上。接着,又学习脚踏式纺线,速度更快。自此,我对纺线着了迷。那段时间,从早到晚,我早上去学校上课,中午吃完饭后接着回教室上课,如果下午要打工,到了打工的点就骑自行车去,打完工后直接回学校接着干,一直干到有人来查教室。当时并没有觉得辛苦,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享受的阶段,没有任何杂念,天天纺线弄作品。我一个人天天在教室里纺线,虽然忍受着寂寞的苦,但当作品完成后,还是感到很有成就感。当时,我的作品《在云中》获得了一个优秀奖,还有奖金。身为留学生,我可以把奖金揣进自己的腰包,但我没有这么做,和日本友人一起用这笔奖金为天美设立了一个“隆英奖学金”。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在中国还是挺有分量的,虽然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当时的姜陆院长跟我说:“韩老师,你这个举措太好了,我非常支持你。”但他又说能不能商量一下,这个奖金不用利息,只用本金,每年发一笔,直到发完。我说没问题,只要这笔钱能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回国后,我的“雪的化妆”系列服装设计作品(见附图)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了优秀奖。这是一组染织和服装纤维相结合的作品,它的结合不仅体现在作品本身,还体现在展示上。但我带着学生在上海展区布展时遇到了难题。主办方只留出一片空地让我们自由发挥,可我没有模特儿,这件作品就难以展示,因为布展时间有限,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就没法展出。这个意外突然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和学生们愁得一夜都没怎么睡。第二天,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跟我上街买东西,行不行另说,现在我多少有点儿想法,你们敢跟我吃苦不?”他们说没问题。我的想法是用腈纶棉把服装支撑起来,于是,我们去买了很多腈纶棉。回来后,我按照人的肢体的扭曲效果,在服装需要填充的地方利用腈纶棉,有挂的,也有粘的,整个布置起来进行展示,这样服装就“活”了。当时,看展的人和布展的人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没见过这样的展示方式。确实,我把纤维和服装两方面的优势集中在一起,这种理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通过这次布展,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艺术创作者,必须具备灵活机智的头脑,时刻保持敏感,思维转换要快,而且做任何事都不能犹豫。对于学生也是如此,不能让他们犹豫不决,有时候适当强迫他们去做一些事,反而能激发出不一样的火花。关于作品,我认为完成并不意味着结束,只有在合适的灯光、空间下去布置,将自己的想法充分展现出来,这才算真正完成。就像我的这批服装作品,如果再有展示的机会,说不定会呈现出与当时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搞艺术创作,不能把自己框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也不能过于拘束,不然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我在做人方面非常自律,但在创作上从不约束自己,始终追求自由表达和创新探索。

当然,我在艺术创作上也会面临一些困扰。比如1995年,我展示了一批手纺作品,可大部分人都不理解。当时我觉得冤,费了那么大劲儿却没人理解。日本的老师对我说“懂的人自然懂”,后来我就琢磨这句话,懂的人能看懂,不懂的人也许能通过作品从不懂变得懂一点儿。艺术创作是要迎合大多数人,还是遵从自己内心想要的、极少数人都看不懂的呢?这是个问题。如果你想做迎合大众的东西,它会趋向于俗,趋向于普通。艺术创作不是,它是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新的开拓、新的境界,如果不这么做,艺术价值就会显得很低。由此我想到,艺术创作不能考虑利益,只要是你认为对的,是你想说想干的就去干,无论有没有经济价值。我觉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价值。这就是我直到现在对艺术创作应该持有的态度的认识。创作必须专心、用心,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要想创作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艺术作品,就需要自觉的努力和不自觉的努力,还要有挑战精神。古人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一味地效仿、学习,那么,在新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和意义在哪里呢?不管做得好与不好,必须要有创新的勇气,不然就会辜负自己、辜负生命。



